功在千秋!原江苏省长惠浴宇回忆建设苏北灌溉总渠和江都水利枢纽
功在千秋!原江苏省长惠浴宇回忆建设苏北灌溉总渠和江都水利枢纽
1951年5月,党中央发出了"一定要把淮河修好"的指示,周总理亲自为治淮制定了"蓄泄兼筹"的方针,作了具体部署。
1950年秋,在华东水利部副部长兼淮委工程部长汪胡桢、中央水利部刘钟瑞司长率领下,淮河入海水道查勘团一行四十多人沿河考察,参加考察的有各方面的专家。
江苏的治淮从何处开始?1951年春,水利部部长傅作义、副部长李葆华带了苏联专家布可夫来,由安徽省委书记、淮委副主任曾希圣陪同,沿着淮河,进行了实地勘查。进入苏北后,我带了熊梯云、王元颐去陪。苏北落后、贫穷,消息闭塞,淮河两岸又是淮海战役的战场,有些农舍的墙壁上,战争年代的宣传口号还在那里:"打到北平去,活捉傅作义!"我大大咧咧地也没注意。傅作义部长要访贫问苦,一头钻进农舍去和农民聊天,布可夫站在门外,指着标语批评说,你们对傅部长太不尊重,明明知道傅部长要来,为什么还留着这个?我这才发现出了毛病,立刻叫行署的公安局长来,派他沿淮河沿线检查,把此类的宣传口号一律刷掉。傅部长巡视完毕,召开了治淮委员会议,回京去了。布可夫留下了,和王元颐、陈志定一起搞江苏的首期治淮方案。1950年4月,淮委工程部提出了"关于治淮方略的初步报告",这是治淮的第一个总体规划文件,其中中下游的整治方案,就是布可夫和各地专家一起研究制定的。
"治淮方略"形成后,刘宠光、汪胡桢带了"方略"应召赴京,由李葆华副部长带往中南海西华厅,向周总理作了详细汇报。
布可夫热情友好,有在苏联参与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丰富经验,能吃苦,也能体谅我们的难处。有一次我陪他在宝应泡大澡堂子,我向他道歉,说我们这儿条件差,只能这样洗澡。他说:你别听他们吹牛,苏联也穷得很,一样有苍蝇、蚊子、跳蚤。他有时也摆"老大哥"的架子,那个时候对苏联专家的态度,往往会被视为政治问题,发生了矛盾,苏联专家动不动就告状,总是国人不对,轻则检讨,重则受处分。我们之间当然也会有争论,但大家都服从科学,从实际出发,重大决策上都能够一致。在华东水利部和治淮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,50年代治淮的总体思路和规划,他是作过关键性贡献的人物之一。"吃水不忘掘井人",对于为中国的治淮事业做出实际贡献的外国人布可夫,更加值得纪念。后来他回国了,时在我念中,不知他还健在否?
根据布可夫和王元颐的建议,我们选准了修建苏北灌溉总渠为苏北治淮第一仗。方案经过淮委的审查,报华东水利部。淮委主任曾山同志在蚌埠听取了汇报,召集会议研究。华东水利部几位副部长刘宠光、汪胡桢多次到苏北来考察。
华东局通知我,政务院要听取汇报。我带了熊梯云、王元颐,淮委派秘书长吴觉同志一同前往。周恩来总理召集政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一起听了汇报。周总理对许多工程的细部问题都详加询问,吴、熊、王诸同志一一回答。王元颐这样的知识分子干部,平时待人接物谦和礼让,见到周总理和这样多国家及政府的领导人,更是拘谨,但一说到他们的本行,就如淮河水一样浩浩荡荡,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样子。他们的话比我们更有说服力。周总理一字一句都作了记录。当时正值志愿军入朝作战初期,中央财政和物资的紧张可想而知。有的副总理、有的部门的负责人表示事情是应该办的,但是就目前中央提供的实际支持的能力看,规模是不是太大了?尤其是蓄水问题,本来上游就有想法,按当时的国力,能解决防灾抗洪解脱人民痛苦就很是勉为其难了,解决蓄水,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水利事业了,能不能以后有条件了再搞?搞这样的工程,用的钱都能铺到香港了。上游有的省的同志也说:我们那儿除涝还忙不过来,你们倒要花钱搞灌溉了?周总理把茶杯往茶几上猛一顿,严厉批评那位同志说:“你的老毛病不改,为什么不好好听听,先分什么你们我们?”
水利部部长傅作义、副部长李葆华都是积极支持这项工程的,我们当然体谅中央的困难,但作为具体实施者又希望能将工程的效益发挥得更好一点。我也不说别的,只说我们苏北是下游,面对大海,淮、沂、沭、泗四大害河,均要出海,我们有义务敞开大门,让兄弟省泄洪,我们一定办到,具体泄多少,按中央指示办。会议上形成了两种意见,一时争执不下。周总理听取了大家的意见,最后拍板说:"苏北人民在战争期间,响应党的号召,上去那么多人,流了那么多血,出了那么多烈士,洪水给你放下海,它够资格蓄一点水嘛!我们应该支援他们……河南上游,以蓄为主;安徽中游,泄蓄兼施;江苏下游,以泄为主,蓄为辅……,苏北五大工程,提得有气魄,我都同意。要保证八百流量,废除归海坝。什么叫归海坝?水大了马上放水淹人就是了,我们党领导的新中国,这样下去怎么行?"他指示我们说:"今天晚上就批准灌溉总渠,你们要像搞新沂河那样搞好这条河。"周总理当即批给大米一亿斤,支持灌溉总渠的兴建。
傅作义部长为了协调好中下游的关系,还专门请曾希圣夫妇和我们夫妻俩到他家吃了一顿。我们这些从根据地来的"土包子",这才知道人世间还真有美味佳肴。
不过,从那次以后,也有一种议论,说我们江苏的水利重大轻小、好大喜功。我们不听那一套,水利事业最得讲究实际,该大就得大,该小就得小。江苏的地形,苏北大面积是平原,苏南大面积也是平原,没有大型骨干工程,小型的往哪里配套?没有大型的水利工程,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人民的事业,只要可能,当然办得越大越好。
回到苏北后,我立即在淮安召集县委书记会议。我传达了周总理"三省共保、蓄泄兼施"的方针。针对一些干部群众中存在的帮中上游泄洪,却要在我们苏北动迁占地出工的吃亏思想,我说:淮河本来是一条好河,封建统治者让它成了一条害河。中央作出了根治淮河的决定,在过去一年中,淮河中上游的人民已经做了许多重要的工程,取得很大成绩。我们苏北人过去为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,现在也要气魄大一点,敞开大门,让河南安徽的水下来,直奔大海!鲁皖两省为治理淮河、支援江苏的水利事业已经提供了很多帮助,现在是我们苏北人民回报他们的时候了。我们三省的人民,同在一条河边,同在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,我们当然要同甘共苦,一起过好日子!
我和钱正英、布可夫会合,再一次考察灌溉总渠的龙头工程高良涧闸的选址。在扬州见面时已经傍黑。我们商量明天的行程,是陆路还是水路?陆路距离短,但路况恶劣,颠得很。水路当然舒服,但小轮船慢得很。熊梯云一个劲动员我们坐船;我性急,能坐车哪肯坐船。我不耐烦:定了坐车,熊梯云你婆婆妈妈干什么?当即决定把船退了,坐车。熊梯云不好再说什么。钱正英看我定下来了,也不说什么,回房休息了。我和熊梯云又商量了一些其他事情,正准备睡呢,熊梯云才告诉我,钱正英已怀第一个孩子,七个月了。我急了,说你怎么不早说呢!我是感觉到钱正英走路有点异样,但对女同志又不好盯住看,再重新安排也来不及了。第二天上路,我让顾静陪钱正英坐一个车,再调了个医务人员来,万一有什么事也好照应。我和布可夫、老熊及随员挤一个车,布可夫对我吹胡子瞪眼,说你们中国共产党什么都好,就是不会照顾女人,农民意识,一点骑士风度也没有。熊梯云和布可夫平时互不买帐,这时倒一致得很。我没话说,是我粗心。从高良涧回淮阴,正下大雨,又不通车,冒雨走了好长一段,更是一路上听他们数落埋怨。
钱正英知道在建国初期上这个工程,来之不易,矛盾很多,离不开她。她不肯离开工地去生孩子,她甚至考虑要坚持在工地,不要孩子,所以她怀孕后一直不离开。直到9月份了,才回上海,10月份就生了。
1951年冬,苏北各县五十万民工上了工地,水利部特派一个水利营来助阵。各县都由县委书记或县长亲自带队。11月下旬,工地上飘起了鹅毛大雪,为了赶工期,各县组织增援,最多时民工达八十万人。一条长一百六十八公里的人工入海通道,开挖土方八千万立方米,排洪量达七百秒立方米,仅用了八十个晴天,就完成了,还同时完成了高良涧闸、淮安运东闸、六垛三座节制闸。

5月和10月,三批世界各国的友人来灌溉总渠参观,他们听了介绍,激动地说:"圣经"上说要修一条通往天堂之路,靠神的力量没有修起来,如今中国人民靠着自己的双手正在修一条天堂之路。他们在水利工地上和民工一起喊号子打夯,干得汗流浃背。
苏联有一位青年水利专家,很漂亮的一位姑娘,听了介绍说第二年夏汛前就要竣工放水,说什么也不信。布可夫在一边说中国人比俄罗斯人要勤劳,能吃苦,她还是不信,盯住了熊梯云要打赌,说第二年她还要来。熊梯云说打赌就打赌,欢迎你再来。第二年竣工典礼,她果然来了,输得心服口服,对熊梯云佩服得不得了,也亲热得不得了。熊梯云打赌时凶得很,这时候成了赢家,胆子反而小了,封建脑袋,连一张照片也不肯跟人家拍,被那个俄罗斯姑娘追得直躲。
在中原和苏北大地上横行肆虐了七百余年的淮河洪水,从此有了自己的入海通道。当然了,从现在的角度看,当时气魄还不够大,作为淮河的入海通道,总渠的规模还是太小了。

布可夫提供了苏联的先进工艺技术,并和王元颐一起设计了我们江苏第一座大型节制闸。这座长七百米、泄洪流量达一万二千秒立方米的的大闸,仅用了九个月就完工了。
当我在冰天雪地却又热火朝天的工地慰问工程技术人员和民工时,我恍如回到了淮海战役的战场上。那时,百万战士和支前的农民,为了自己的翻身解放,前赴后继;而如今,他们为了自己的和子孙万代的幸福,创造了何等惊人的伟业!降龙缚蛟除民害,挥笔蘸血改地图,我为我是他们之间的一分子而甚感自豪。
战争年代结束后,50年代60年代,再也没有比水利工程那恢宏壮观的事业更令我激动的了。
江苏大兴水利,得到了中央和华东局、淮委的全力支持。曾山同志是华东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,又兼任淮委主任。他在治水开始时,就强调要尊重科学,尊重专家,尊重工程技术人员。在组建水利队伍时,各级党委都认真贯彻了他的指示。当时,我们党内像吴觉、钱正英、熊梯云这样既懂行又能独当一面的水利人材并不多,但因为能够广纳贤才,尊重党内外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,使他们有职有权,使他们有用武之地,我们很快地就集聚了一支门类齐全、人材济济的水利科学队伍。
曾山同志的倡导,还培养了我们科学决策、民主决策的良好作风。每一个工程,都要组织大批科技力量反复地实地勘查,各级领导都自觉参加;也都要经过反复论证。在论证过程中,难免有不同意见,有时还尖锐对立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在决策前,听取各种意见、各种方案的争论的。水利工程,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巨大,稍有不慎,便会造成巨大的浪费,甚至产生负效应,甚至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。我们一开始搞水利,除了有政治优势外,对水利是十足的外行,即使后来学了一点,和专家们比较起来还是小半瓶子醋。不懂就是不懂,切不可装懂。在决策过程中,我们有意营造民主讨论和争论的空气,往往最好的决策和方案就在各执一端的争论中产生。经过反复争论再决策,心里踏实;大家一条声拥护,不说反对意见,心里反而紧张。我们和专家们是战友和朋友,为了同一事业同甘共苦,无论是党内党外的专家,以至和苏联专家布可夫,都有过面红耳赤的争论。争论,促进了我们的事业和友情。
淮委设在蚌埠,是统管鲁苏皖三省治淮的前方指挥部,下属单位有一百多个,仅1951年一年就接收了一千三百多个水利或相关专业的大中专毕业生,更不用说通过各种渠道请来的专家学者了。在三省工程集中的时期,淮委指挥、调度着所有的工程,指挥着几百万军民。淮委建立初期,从曾山同志到各省的领导,都另有一摊工作,真正在蚌埠淮委主持工作的,是吴觉、万金培、钱正英三位同志。吴觉任秘书长,负责主持淮委的日常工作。千军万马,千头万绪,他们指挥、调度得井井有条。抗战初期,我在大桥,吴觉、汤曙红、陈克天在淮海拉起了抗日队伍,曾和我联系过。后来黄克诚同志率军南下,他们划归黄克诚指挥。吴觉是老党员,我对他一向敬重。他对前期治淮作出了杰出的贡献,我正为上级机关有这样的好搭档而庆幸,他却突然蒙受不白之冤,被罚到三门峡去了。我们好像注定前半生没有缘份,直到"文革"后,他到南京工学院任党委书记兼院长,我们才得以常常在一起相处。他仍是知识分子的好朋友,在南工赢得师生们的爱戴。钱正英同志任水利电力部长时,想倚重吴觉同志,请他重返水利战线,惜他历经磨难,身体已不堪重负了。
我们依靠各方面的力量大兴水利建设,而各方面的有识之士,都把消除水患、兴修水利当做自己的职责。江苏建省后,计雨亭任江苏第一任水利厅长,陈克天、熊梯云等同志任副厅长。计雨亭同志是我们党在战争年代的的老朋友,那时他和苏北的一些开明士绅,如韩紫石、朱履先等,就重视和倡导救灾治水,在那个年代,当然不可能有大作为。解放后,他和我们一起风里来雨里去,抗洪抢险,他抢着到第一线去,有时为了照顾他,请他在后方协调指挥,他还不高兴。他做水利厅长,既有经验又孚众望,我们党内的同志对他都很尊重。所谓知心朋友,并不是做了什么官再交朋友的,像计雨亭这样,是我们在患难中的朋友。
党的事业需要团结最广大的人民,这不仅是水利事业,但党内"左"倾、右倾的影响,又严重破坏我们队伍的团结,使我们的事业受到极大的伤害。
吴觉这样的老同志蒙受不白之冤,淮委的工作自然会受到极大的影响。水利工地正热火朝天,熊梯云突然被扣起来审查。熊梯云违反程序办事是有的,一度时间内,民主作风差也是在干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的,但处理过重,甚至给他乱扣罪名,例如说他是"经济大老虎",完全是莫须有。几十万民工在冰天雪地里激战方酣,突然自折一方主将,当然要影响工程进度。我为此事大动肝火,后来一直吵到华东局,几年后才算有了结果。那个时候"三反五反",反贪污反浪费理所应当,但一搞运动就过火。泰州地区专员、泰州治淮总指挥黄云祥也被指为"老虎",说他包庇银行的行长,而那个行长竟然贪污了六十亿水利款!真是胡扯淡,泰州所有银行的钱加起来也没有六十亿,整个苏北的水利专款也没有六十亿。这样荒唐的事情,上级领导竟然也相信。
灌溉总渠完工后,苏北五大工程陆续筹划上马。洪泽湖大堤、运河大堤和江海堤防的加固,淮沭新河的筹备工作……大家都忙得了不得。我派苏北行署水利局的总工程师陈志定去安徽开水利协调会议,说好了几天就回来的,等来等去不见人归。我打电话去查询,说是陈总被当逃亡恶霸地主抓了起来,据说还要枪毙,吓得跟他去的随员连电话都不敢打。当时正在"肃反"的高潮,前不久我还被人批为"右倾",差点说我是"双皮老虎"(指思想、经济),但我和陈志定同志共事,亲眼目睹他学识高超、敢于负责、为水利事业吃尽辛苦、甘愿赴汤蹈火的精神,他和王元颐等专家同志是我们在苏北治水不可缺少的关键人物。那时我虽然还不详细了解他的身世,但我知道他年轻时师从郑老先生,一直在忙治水,有什么空去行恶作霸呢?我想不通,连夜打电话找到中央"肃反十人领导小组"的陆定一同志,向他告状。我说陈志定即使是恶霸地主,也是我们江苏人,又工作在苏北,要枪毙也该绑回原籍来枪毙,轮不到安徽来帮我们"肃反"。我又打电话给调往中央任水利部副部长的钱正英同志,请她向中央证明陈志定的水平和贡献。钱正英立即向中央反映了情况。经过多方努力,陈志定同志终于被保了回来。安徽有关人还跑到华东局去告我"右倾",说我"包庇逃亡地主"。一年后,他们真的抓到了安徽籍的逃亡地主陈志定,才告诉我当时抓错了同名的陈总,此事才算了结。
我们的水利老专家们真是好!陈志定是被绑着送回来的,受了这一场差点要命的惊吓,一句牢骚也没有,立即领了人去查勘工程选项。那时候大家普遍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,陈志定曾经说过:我们越是早点在水利工地上多动一锹土,苏北人民就多一分安全。他们根本没有空去找人诉说个人的委屈。
50年代,没有先进的测量手段,水文资料残缺不全,水道年久失修,到处不通,陆路少且差,车舟均不便。往往一个较大工程的规划设计,要经过大量的实地踏勘。风里雨里雪里泥里,大部分地段全靠脚走。当民工们走上工地开工时,专家们率领的勘察队测量队,已经走了几万里路了。
50年代后期,钱正英同志带了水利部的同志会同江苏的专家勘查规划,她指出灌溉总渠泄洪量不足,而新沂河泄洪仍有潜力,她向江苏省委提出开挖淮沭新河.要熊梯云做论证,这是江苏第一条跨流域调水的工程。工程方案经省委、淮委层层批准,后来,刘顺元带队去京向周总理汇报。要搞建设,财政总是紧张的,有的领导同志提出耗巨资搞跨流域调水,过去没有先例,现在条件还不具备。刘顺元争辩说:淮水北调,不仅有利于苏北的农业、工业和交通,枯水期,可以把水一直送到新海连,支援那里的海军设施和部队,有利于国防建设。周总理称赞说:搞水利工程,还想到支援国防建设,过去也没有这个先例,江苏的同志有全局观念,想得好。淮沭新河,这个名字一语双关,起得俏皮,把水送到新海连,洼地改制,这个办法好。当即就批准了。若不是钱正英提出并支持开挖淮沭新河;刘顺元力争,又强调了这项工程的国防意义,江苏连年上大工程,当时就批准修淮沭新河,是很难办到的。不久,又按中央统一部署,建立了整治大运河指挥部,由王治平任主任,陈克天为副主任。王治平领受任务后,陪着水利部的领导,冒着风雪,从苏浙交界的南浔一直踏勘至鲁苏交界的不牢河,他当时已六十岁出头了,且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。我听说后,急得差点撤了他的职逼他去疗养。
百行百业中,水利行业是最艰苦的行业之一。我们的水利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,放弃了优裕稳定的生活,成年累月成十年成几十年地生活工作在野外,在工棚里。民工们可以按期轮换,他们却自愿服"无期劳役"。夏天,芦席棚里到处长霉,冬天,被褥下结着冰霜。每逢抗洪抢险,哪个河段最危险,他们就坚守在哪儿。他们为水利事业献出了青春,献出了一生,甚至献出了生命。王元颐同志堪称为他们的代表。淮沭新河和整治大运河工程上马不久,就碰上了"三年自然灾害",到处闹饥荒。我在省委分工救灾,在南京坐不住,除了开会,就一直在重灾区。我去大运河工地视察,民工们一天只有4毛钱工钱,几两粮食吃,一百多斤的担子每天要挑一百多担,哪能吃得消?工程进度明显慢了下来。工地上已经完全没有了开工时那种热火朝天的气氛。我找了陈克天、熊梯云来问情况,他们说不仅大运河工地,所有的水利工地都严重缺粮。我和刘顺元商量了,又找计委刘和赓来,说:水利工地要保证每人一天三斤原粮,不然把你送工地上去饿肚子挑河工。刘和赓一看没有还价的余地,连忙去办理。我也知道国库粮已全部调往灾区,刘和赓手上也没有多少粮食,留着应付紧急灾荒的救命粮,他的难处我一清二楚。所以我只好不和他商量,下命令让他执行就是了。
工地上的粮食暂时解决了,我问熊梯云,王元颐、陈志定这些同志成天往工地上跑,工作非常艰苦,生活过得去吗?老熊说:王元颐家里人口多,一天只喝两顿稀的,还不能保证,已经饿得浮肿了,在工地上就是不肯回来。我自责事太多,竟是疏忽了!我说熊梯云你赶快送一千斤大米到王元颐家去,要亲自去,以后要按月补贴,再看看陈志定等几位老专家,他们可是我们水利界的宝贝,一定要尽可能照顾好。
但还是太晚了。1961年,王元颐同志积劳成疾,不幸病逝了。他的逝世,不仅江苏水利界尽皆垂泪,不仅是我们这些参加治水的老战友、老朋友伤心不已,苏北特别是两淮流域的干部群众都像是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一样悲痛。淮阴在为他开追悼会的时候,地委书记孙振华如丧考妣,哭得透不过气来,会场上哭成一团。我到他家去慰问,看到他留下的简朴的家和孩子,陷入深深地自责中:我们对这样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知识分子干部关心得太少了!唯一能使我感到安慰的是,他的儿子王厚高同志已经继承了他的事业,成为我们江苏出类拔萃的青年水利专家。
到了50年代中后期,王厚高、许荫桐、方福钧等年纪稍轻一些的同志,经过艰苦的实践锻炼,在老专家的培养下,已经能够独当一面地担任大型水利工程的总设计和施工的总指挥了。

江苏经过多年治水,群众、专家、领导摸索出行之有效的经验,叫作"四分开一控制",搞了防洪、防潮、防涝、防旱、防渍五套水利系统。这个经验报到省委,江渭清同志极为重视,立即在苏州召集全省的水利会议加以推广。江苏水利建设的成绩,是和各级领导班子对水利事业的重视分不开的,那时无论哪一级领导干部,完全不懂水利或不重视水利,是根本混不下去的。
60年代初期,周总理在上海、北京召开了两次关于南水北调的会议。那时安徽在淮河干流修建了蚌埠闸,这使地处下游的的江苏意识到:淮河的水可用不可靠,一旦大旱,上游的水下不来,灌溉总渠失去作用,淮沭新河和大运河也发挥不了效益。好在我们有了这两条南北通道,何不把长江的水调上来呢?方案经过论证报中央后,引起周总理的重视。周总理说:调水要打破省界,哪里缺水就往哪里调,这个工程最后完成我恐怕是看不到了,能够听到你们的汇报已经是很高兴了。他亲自批准了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。
1977年,我站在江都水利枢纽雄伟的大坝上时,想起周总理的话,我第一次体会到周总理话中感慨的意味。周总理已逝,我们也老了。但世上只要人类还存在,人就永远要和水打交道。我们的水利事业,将由我们的后人继续下去,我相信,他们会干得比我们更好。

-

- 妖怪名单阿疯和龙三元的故事:龙百年为一岁,人百年为一生
-
2024-08-26 16:49:46
-

- 上百亿遗产险些被渣男骗光,亚洲女首富龚如心的遗产风波
-
2024-08-26 16:47:32
-

- 薛国的终结与历史的反思
-
2024-08-19 17:53:20
-

- 陕西地区高尔夫的起源与进展
-
2024-08-19 17:51:05
-

- 长屋王之变的经过是怎么样的?长屋王之变的最后结果是怎么样的?历史
-
2024-08-19 17:48:51
-

- 谢安:东晋的杰出政治家与淝水之战的英雄
-
2024-08-19 17:46:36
-
- 萧绎:以兰入诗的梁元帝:杜甫草堂兰花展
-
2024-08-19 17:44:21
-
- 仆固怀恩是忠臣吗?如何评价仆固怀恩
-
2024-08-19 17:42:07
-

- 钧台之享简介 历史上的钧台之享 钧台在哪历史
-
2024-08-19 17:39:52
-

- 智慧超人宋太祖赵匡胤有两个儿子,为什么把皇位给了弟弟
-
2024-08-19 17:37:37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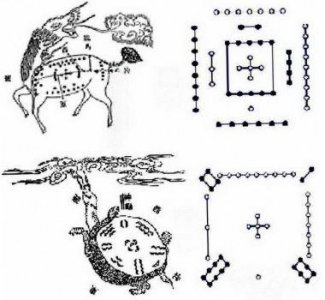
- 诸葛亮到底有几个子嗣?
-
2024-08-19 17:35:23
-
- 美女的结局不圆满貂蝉最后竟是这样死的
-
2024-08-19 17:33:08
-

- 八旗将军假如和提督相遇的话到底谁给谁行李
-
2024-08-19 01:53:07
-

- 窦太后与汉景帝:权力背后的历史真相
-
2024-08-19 01:50:52
-

- 福建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田径比赛和运动员?
-
2024-08-19 01:48:37
-

- 张飞到底长什么样子张飞美男子的观点是怎么来的
-
2024-08-19 01:46:22
-
- 为什么卫青死后整个卫家都被汉武帝刘彻诛杀
-
2024-08-19 01:44:08
-

- 保加利亚历史上都有哪些重要事件和人物
-
2024-08-19 01:41:53
-

- 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初期对知识分子礼遇有加,后来为什么要将他们斩杀
-
2024-08-19 01:39:38
-

- 历史人物:王彦超与智慧超人宋太祖赵匡胤之间有什么渊源他最后的结局如何
-
2024-08-19 01:37:24



 哑剧是什么
哑剧是什么 诗人屈原活了多少岁 屈原后代如今在哪里
诗人屈原活了多少岁 屈原后代如今在哪里